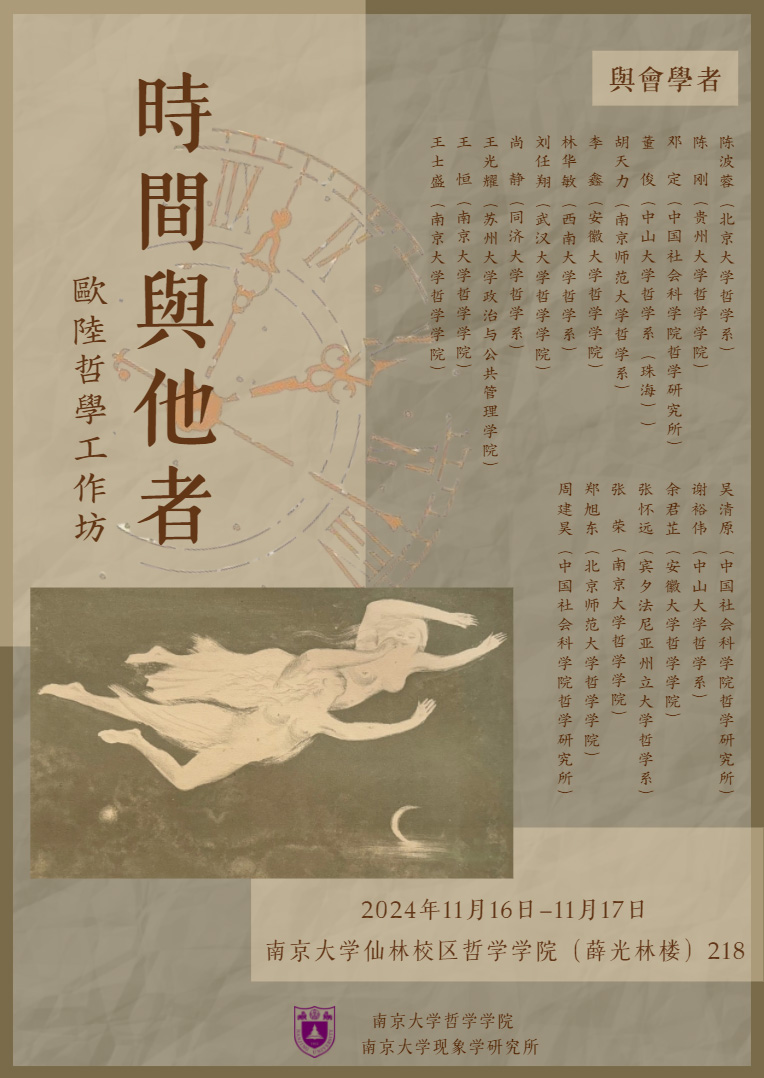讨论时间:2023年10月30日
领读学者:Leonard Lawlor
录音整理:张宇涵、崔天
字数总计:25000
完读时间:2小时25分钟
1 引论
刘任翔: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Leonard Lawlor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人,带领我们进入德勒兹思想盘根错节的迷宫。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已经对德勒兹或是现象学传统、欧陆传统有所了解。总的来说,我觉得Leonard今天要做的事与我们在曾经的议程中所关心的东西紧密相关,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时间的内容。
Leonard Lawlor教授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宾州州立大学有很多校区,其中最大的是University Park。
L. Lawlor:是的,是那个大校区。
刘任翔:这也是哲学系的所在地。Leonard在他的早年研究中对法国思想家很感兴趣,比如福柯和德里达,他就这两个思想家写作了很广泛的著述,你们可以在他简历的出版内容里看到这些著作,很多很有意思的书。我尤其喜欢那本论述内在性(immanence)的书,它的名字是《内在性的内涵》(The Implications of Immanence)——两个非常有趣的词,我们也能从中收获许多。
以及,我想大概是十年前左右,Leonard逐渐转向了德勒兹的思想。我认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德勒兹思想中的理论层面。他现在正在写作一本新书,要把德勒兹理论层面的工作扩展到伦理的维度。提前分发的文本,是这本叫做《论龃龉》(The Disparate)的书的绪论。
L. Lawlor: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们差不多花了一星期才协调好要来做这个讲座,能来到这里我也非常感激。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在北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和妻子去了长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旅行。
感谢任翔的介绍。他说得对,我正在写一本叫做《论龃龉》的书,我马上会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这是一次处理德勒兹的理论化著作的尝试,比如说《差异与重复》以及其他1960年代的书。他在1960年代的一年之内,一下子出版了三本书。1968年有一本关于斯宾诺莎的大书(《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还有1969年的《意义的逻辑》。
在我的书里,我会讨论这三本著作。我想做的是,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化的书,揭示它们可能暗含了某些伦理学,即使德勒兹从来没有写作过伦理学。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他写过的某些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伦理学,比如说,如果你们研究过德勒兹的话,那这可能是人们关于德勒兹已经知道的:在《意义的逻辑》中,他一度说,“要么伦理学毫无意义,要么这就是伦理学想要说的,伦理学只会说:莫要配不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莫要配不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在这本正在写作的、我的第九本有关德勒兹的著作中,我尝试做到的是从一个陈述中发展出德勒兹的伦理学——“莫要配不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说法是否定性的,这看起来也是一个谜团,因为你并不知道肯定性的东西是什么。他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他告诉你如何能够不配不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该做的事情,以及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才能配得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这就是我想要归到德勒兹头上的一种道德理论或者伦理学。
2 从德勒兹出发的伦理学
L. Lawlor:某种程度上,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是一次对德勒兹思想的创造性挪用。我不是很确定我是否总是忠实于德勒兹的思想,以及,这本书中我持有的某些观点可能更多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总的来说,相对而言,我最近认为在英语中我们有两个词语用来谈论道德,一个是道德(morality),另一个是伦理(ethics)。而伦理是一个希腊词汇,道德则是一个拉丁词汇。现在“道德”倾向于被看作一系列如何做好事、做好人的规则;鉴于“绝对命令”与康德就各种规则谈到的那些东西,人们通常把他的道德哲学放在“道德”这个序列中。而“伦理”呢,它来自ἔθος(ethos)这个词语,它的意思有点像行为模式,意味着生活的方式;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德勒兹的伦理学更多地位于“伦理”这一侧,给予我们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系列规则。但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做的其实正是把某些规则也归给德勒兹的伦理学。事实上,我要把某些“命令”归给德勒兹。所以我将要挪用一些康德的道德哲学来解读德勒兹的思想,即使许多德勒兹学者会认为这是对他思想的违背。但是我有文本证据来支持我的想法。
我在这里处理一些手写的笔记。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陈述,关于德勒兹的伦理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强力(power)的伦理学。power,在英语里有两个意思,在法语中则有两个不同的词分别对应它们,pouvoir与puissance。在英语中,power这个词有一些歧义:power可以意味着“凌驾于某物的权力(power over)”,在法语中表示这个意思的词是pouvoir;但同样还有一个词,意味着以“我能(je peux)”的方式去行事,它的意思是“我能做某事”,在法语里是puissance,以及power这个词的这一部分在英语里可以被理解为“潜能(potentialities)”——这正是德勒兹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称其为伦理的东西就是实现某人的潜能的能力。
如果你们了解一点斯宾诺莎的话可能会知道,在斯宾诺莎这里,德勒兹让我们关注的,我认为应该是《伦理学》第三部分靠近开头的地方。斯宾诺莎说,我们仍然“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事”,而德勒兹几乎在他每本书里都采用了这句话,这就是他想说的。所以他的伦理学事实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实际去做什么。正如我上个星期在北京大学的讲座里所说,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德勒兹的哲学。当你理解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它改变了你思考你自己、思考如何行事的方式。甚至我们不用进行伦理学的思考,他的理论思想就已然在将我们理解自己的不同方式解放出来。我有些离题了。总之,德勒兹他是一个西方哲学、西方思想的伟大批判家。
当他和精神分析家菲利克斯·加塔利一起写作那些很有意思的书的时候,他们相当严肃地批判了西方的政治局势,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真正反对的东西——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一种形式主义——它们的批判才是解放性的。正如我们所知,在英语中你可以玩一个这样的文字游戏:“你必须遵守(conform)某些形式(forms)。”这个打破规范或一致性的观念已经被许许多多哲学界之外的学者所接受。所以,在英语世界的哲学系里,德勒兹没有被研究得很多,而在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地理学系被研究。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他事实上也在被商学院研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本人就去过一个在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的德勒兹会议,十五年前,我就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商学院主办了这么多会议来研究一个疯狂的哲学家!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解放性的思维模式正在占据更多学科、思维领域,更多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但有一个我一直强调的、对于德勒兹伦理学十分重要的事情是,他同样也是一个关于“无力(powerlessness)”的哲学家。如果你去读文献、读研究德勒兹的学术作品,无力这个概念在文献中并不特别被强调,而我一直强调它。事实上在今天你可以很快地说:“哦,德勒兹是一个“强力”的哲学家,而这意味着我们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潜能”,大家就会觉得很不错。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无力的经验,就谈不上潜能的实现。我会走得更远一些,我会说:没有磨难,就没有“我能做什么”的经验。如果你去读研究德勒兹的学术作品,我认为你找不到任何人这么说;但我同样还是会说,我有文本证据来支持我声称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对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一点导入。
3 “龃龉”和“差异”之异同
L. Lawlor:我们已经谈了十分钟,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谈一谈这个伦理学,但我现在要开始谈他的理论哲学了。以及,我们人数不多,所以请不要不敢提问或举手,需要时我会停下来。我很乐意进行一些交流,而不是我对着你们讲,所以不要害羞,如果能回答问题的话我会非常开心,即使我完全不懂你们的问题也完全可以,我会尽力解答。
好,让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标题,《龃龉(Disparate)》,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法语词,le dispars,这就是文本中德勒兹使用的词。在英语里把这个词当做名词来用有些晦涩,在法语中也是,这不是一个在法国能经常听到的普通词汇。特别地,在《差异与重复》这本书里,他基本上和“差异”含义相同。显然,这本书的标题是《差异与重复》,“龃龉”是德勒兹在这本大书中用来谈论差异的许多词汇中的一个。但“差异”有它自己严格的定义,“龃龉”则更加严格。“龃龉”实际上指向经验。
我不会讨论太多你们已经很熟悉的西方哲学知识,如果你们理解的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人类的官能学说分为几个部分,他把其中一个叫做感性论(aesthetics),这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味着感觉(sensation);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艺术哲学;而对于德勒兹,这个词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含义:它意味着我们感觉到的东西,但同样也意味着我们我们关于绘画、诗歌、建筑等等这一切普遍来说所想到的东西。但龃龉这个词它的严格含义明确地指向感性论/美学、指向我们感觉到的东西。
你们研究过现象学,这也是与德勒兹思想有交集的地方,现象学,因为他对描述经验也非常感兴趣,他也会在书里多次使用“现象”这个词和它的复数。但他真正关心的是,龃龉之物是何时参与进来的。这里有一些我写过的句子:“他想要理解是什么给予了所与(what gives the given)。”所与,这是一个现象学术语,它的意思是我们见到的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被动接受到的东西,对吧?他同样用康德哲学的语言说过,他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那最接近现象的本体(noumenon)。“接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能够感觉到它、差一点就能感觉到。不过,对于康德的第一批判来说,本体是一个我们无法接触的思想对象,人类知识无法接触到本体、那产生了现象的东西。康德把它叫做“自在之物”,相对于“为我们的物”。但德勒兹说这个本体是最靠近现象的东西,他认为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我们能够接触到、能够经验到的不只是所与,还有那给予所与的东西。所以,这虽然是康德哲学的语言,却不是康德主义的,因为他想要把本体与感性拉近,把它置入有关我们实际能感觉到的东西的感性论/美学。
那么,我将会通过龃龉的含义来解释它。想想看,如果你们要研究这本书,你们会看见龃龉这个词,然后是差异这个词。“差异”更多针对存在论(ontology):当他谈到存在是什么时,差异就会在那段论述中发挥很大作用。但他要说的是经验、感性,于是就有了龃龉这个词。存在论,你们听到了这个词的结尾,logos,它是一个希腊词汇,充当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所有罗曼语等等语言中逻辑这个词的词根。所以差异更多针对逻辑,龃龉更多有关于感觉。再一次,他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来做出这个区分。
4 思想的图示
L. Lawlor:还有一个理解龃龉的方式,如果你们读了这本书或者德勒兹其他的书,我觉得你们应该能够找到许多图示,比如他和加塔利的书《千高原》。你们真的需要把握住这些图示,因为他创造的概念对刚刚爱上他的哲学的人来说的确是极端复杂和晦涩的,你们可能也处于这种阶段。有些时候是会有些哲学家,你刚开始阅读他们的时候会非常兴奋,然后你就会意识到“我完全没看懂这个哲学家在说什么。”它确实晦涩,不过还是有些地方有关它的写作方式,到处都有你能理解的小线索、小东西。正如你会引用这些地方,你会想“这值得我克服晦涩的努力”,而这也是我读德勒兹时的体验。不过,这些图示是一些小线索、一些你很容易理解的东西,但是它们指出了一系列概念性定义、概念内部发展的方向,而这些概念非常难理解。
所以你们必须把握好这些图示。这里就有一幅给你们的图。你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艺术,就我所知范围内的中国艺术,也包括西方艺术、希腊艺术、罗马艺术、法国艺术——是对称让其变得美丽。对称的处理大概要么是两边基本相同要么是画面两边具有一种平衡。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实际上成为了美的定义者,脸的美丽,在这个定义下,眼睛在美丽的脸上占有相等的空间,也就意味着眼睛的形状之间必须成比例,脸颊和嘴唇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实际上给出了他对美丽的定义,基于平衡,甚至有时需要计算——鼻子的宽度要多少厘米、眼睛要多少厘米……不过他当然不知道现代公制,但这就是对称性。进而我们通常则会认为不对称是一种对称的缺乏,对吧?于是,我们会说:一个坏艺术家、平庸的艺术家、不擅长艺术的艺术家找不到平衡的比例,坏艺术家会塑造出扭曲的面孔,比如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又在那里——你会马上想到毕加索,对吧,这个试图挣脱“美丽”模式的艺术家。但通常看到他的画的时候你会想:“啊,其实不是很好看”,你会觉得画中的事物没有处于平衡的关系中,所以你可能会想不对称确实是一种对称的缺乏。但对德勒兹来说重要的是,他会把这个关系倒转过来,他可能会论证说:不对称并非一种缺乏,反而完全是肯定性的,事实上是它产生出了对称。
我们再看到这个图示——最接近现象的本体。给予所与的东西是不对称。德勒兹关于不对称说了很多。就像,随着我理解德勒兹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点惊人的是,我现在找到的一个表述是他说“给予所与的东西是混沌(chaos)”。一个很古老的希腊词汇,不过我们的当代生活中也有一些描述混沌的图示,而这正是惊人的地方:他在1968年使用了这个词语,这是他谈论不对称的一个方式。
用不同的话来说,不对称是“深渊(abyss)”;他还用过“背景(background)”这个词,但同样有点惊人,因为他实际上用这个词来指“深度(depth)”,但不是作为知觉的第三个空间维度的那种深度,而是比我们能够测量的一切都更深的那种深度。我们会认为深度是一个普通的空间范畴、是一种我们尚未经验到的长度,但德勒兹说,不是,“它很深”是在说某种空间维度之外的东西,它比空间的维度更深。
5 背景、基础与深度
L. Lawlor:你们会发现我们正在进入一些越来越晦涩的东西。但德勒兹认为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个深度。我们可以以一些特定方式在特定条件下把它带到我们跟前来,对吧?比如日常生活里我们习惯于我们看到、谈论的那些东西,以及其他有感知能力的生物,比如猫。德勒兹说大概现象学有时会把这些称作背景(background)或视域(horizon)。你们如果在这附近走走,如果雾不是很重的话就能看见那些美丽的群山,北京的西北。那些山离这里非常远,相当地“深”。这可能能帮助你们想象一下。
我们回到深度的含义,而我想在深度的主题里引入一个词,“背景”。有些像这样的词可能会让德勒兹的思想变得相当难懂,但我坚持认为要理解这本书的话这些词是很重要的。德勒兹写了很多东西,你们可能见过“充足理由律”这个短语,它来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第一次把它规定为今天的形式。充足理由律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原因,莱布尼茨补充道,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不想深入莱布尼茨但他的确就其自身的研究主题来说就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因为他认为,如果要找到充足理由,即使只是靠近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充足理由,我们都需要把自己的知识设想为实无限的(infinite actually)。但这个充足理由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种谈论基础的方式。你们如果了解近一百年的当代哲学,欧陆、法国、德国以及英美哲学,大概会把所有这些哲学归为反基础主义。德勒兹也在这个行列中,但他要找的事实上是真正的基础。
那么,你们听到了这个英语单词,基础(foundation),而现在我要讲点法语了。在fondation(基础)这个法语单词里,你们可以听到它的词根——和英语相同的拉丁词根(fond-)。而对于法语单词fonder(赋予根据),我们在英语里有两种方式去说赋予根据、to found。但这种形式人们其实不会经常说,人们常说的是“to ground”,它基本上是“to found”这个英语直译的同义词。《差异与重复》倾向于采用“to ground”而不是“to found”来翻译fonder这个动词。然后对于fondation,我们还有另外的词,fondement(根据),而这个才是法语里严格意义上去说“赋予根据”或者“根据”的名词。还有一个词的意思是背景,le fond(底部),词根也是一样的。le fond是一个习语,可以用在一些法语惯用表达里,比如“quelque chose du fond”的意思是“从深处来的东西”。有些人会认为给予了所与的东西就是在深处的东西,比如海洋的底部、海洋底部的深渊。
我们继续,深度的法语单词是profondeur。在英语里我们也有一个单词profound,如果你说英语的话你肯定会用这个词,但是大部分说英语的人不会想到深度这个含义。他们会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难以理解”。“你说的东西很profound”的意思是“哦,这个很严肃,我得努力一下理解你说的东西。”如果你和这个人多聊一会儿,他可能还会说你的思想很“深刻(deep)”。他们不会想到的是关于事物的空间性知识,比如“哦,这么难的思想我需要去穿过它。”但在法语里,如果你用profondeur这个词,它就意味着空间性的东西。它意味着作为空间里一个维度的深度。
那么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词都是如何相关的了。我们有一个动词,fonder,赋予根据;我们有fondement,用来表示根据。还有一些词:fond,底部或者是背景;profondeur,深度。但德勒兹还用过一个词,在法语里非常不常见的词,effondement(脱根据化),你们可以听到它的前缀,ef-,有点像de-,所以这个词大概是“去-根据(de-foundation)”或者“非-根据(un-foundation)”。它是根据的崩溃。
刘任翔:你刚刚谈到了那些词语的丰富内涵。你从不对称这个词开始,然后提及了地狱、深渊、死亡、背景等等,然后是一些和fond相关的词语。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那个概念,effondement。它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过程,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而对德勒兹来说,它似乎才是真正的根据。
L. Lawlor:没错,真正的根据其实是他使用的这一个另外的词。它其实是一种疯癫、错乱的形式。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会使用“非理性的(irrational)”这个词,它是一种“充足非-理由(ir-reason)”或者“充足去-理由(de-reason)”,用以转变莱布尼茨甚至是斯宾诺莎那里的充足理由概念——让我们假定斯宾诺莎在没有明确命名的情况下也应用了这一原则。但是其实通常来说,对于17到19世纪的现代哲学家来说,充足理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那个至高理性,对吧?上帝总是有解释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理由,但德勒兹并不打算沿着这个神学的方向前进。他只想进入这个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不一样的经验。这就是我想引入的东西,充足非-理由、去-理由的玩法,我同样还会说这就是真正的充足理由。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真正的存在理由。
刘任翔:所以它和福柯书名里的“非理性”(déraison)内涵很像吗?
L. Lawlor:是的。
刘任翔:那么déraison(非理性)恰恰是某种raison(理性),是这个意思吗?
L. Lawlor:我在想,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我可以把它用到充足理由律的解释中。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谈谈德勒兹。福柯这本书是1961年的,他那一代几乎所有法国哲学家都以极大的兴趣和赞赏读过了这本书。如果你们认真研究的话,那是一本惊人的书,非常非常长的的书,你甚至可能需要一个月来读它。但你们知道,所有人都把这个déraison概念当做某种理性的“反常(perversion)”,“变形”,看起来是非理性的。这当然是福柯著作的一种回响。
刘任翔: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个概念叫“Abgrund(离基深渊)”,而Abgrund就是某种Grund(基础/根据)。它同样通过自行分解来赋予根据。这和德勒兹的观念相似吗?
L. Lawlor:完全是相同的观念。我在上周的北京大学讲座上说过,德勒兹几乎没有提到过海德格尔,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同时很了解海德格尔又很了解德勒兹的人来说,很难忽视他们的相似之处,即使德勒兹从来没有把他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作品联系起来——几乎从来没有,偶尔有几次,但显然意思是差不多的。
刘任翔:谢谢。
L. Lawlor:还有问题吗?
杜昕蕤:我想知道déraison是怎么变成raison的、它是怎么运作的。
L. Lawlor:如果你想要把raison、理性当作事物如何以及为什么存在的解释来思考,那么德勒兹会说事物通过混沌、因为混沌而存在。所以我在说“充足非-理由律”或者“充足无理由(déraison)律”的时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此外,如果你认真阅读了德勒兹很多书,你会发现“根据”的问题几乎在他的每本书里都有出现。基本可以说他对基础的问题很感兴趣;但仍然要说,他感兴趣的是生产性的那种根据。所以,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讲到对这个过程的详细解释。
6 避免乞题:根据的异质性
L. Lawlor:然后我们有一个有关于根据的问题,非常地传统的西方哲学的问题。如果你们上过逻辑学课,即使是非常初级的逻辑学课程,你们的逻辑学老师教给你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你们的论证中要确保没有“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的谬误。它被称作思维方式错误或者推理方式错误的谬误。它还被称作“循环论证”的谬误。德勒兹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在传统逻辑学里,我们把它称作谬误。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哲学传统里,从柏拉图直到十九世纪的尼采,都把某些经验性的东西(比如某个对象)普遍化了,使它成为个体事物的根据。
有许多途径来做这件事。在西方,我们会诉诸“人类的内在思想”,我们把它叫做主体性。有一些现代哲学家会谈到经验主体性,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验的东西——你就是你正持有的思想。这是经验性的,位于时空之中,位于你的身体里、就现在。同样我们还有先验(transcendental)主体性,还有现象学。现象学对于先验主体给出了很有意思的发展,它采用和内在生命一样的结构,但移除了时空,把它普遍化——我们所有人思考的普遍结构就是先验主体性。但你们同样可以看见问题,那就是这种先验主体学说正在用经验主体的结构来解释先验主体。
我们得到任何结果了吗?德勒兹说没有,因为一个真正的根据不能和被它赋予根据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逃出循环论证、找到真正根据的方法。根据决不能与被赋予根据者相似。
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的循环:我们从一处开始,随后只是再回到这个地方说些同样的话,只是把同样的东西普遍化了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乞题,它们都是说的同一件事情。
而这里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根据,因为你之前把被赋予根据者当成根据。它向“什么是根据”这一问题“乞求”(beg the question)其答案。你们还没有找到答案,因为你们给出的答案与被赋予根据者是相同的东西。
现在德勒兹想要打破这个循环,他的整个思考就是为了打破这一循环。而你们看到问题就出在这个“相似关系(resemblance relationship)”上。这个循环论证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有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很像……我接下来用几个术语。我们有经验主体性、先验主体性,但这先验主体性却与经验主体性是相似的,而你仍然找不到它们之间相似关系的理由。所以德勒兹想要从这种相似的观念中摆脱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差异与重复》——因为我们看到的关系是相似关系、相同关系,甚至就是同一关系,但根据与被赋予根据者之间必须有差异。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当我们使用“结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日常思维模式的结构,可能某种更深刻的先验思维模式也是同一个结构——我们究竟想要说什么?
显然,根据肯定不能处于相似关系中,绝对不能是取一个现成东西的形式然后把它复制至此的结构。真正的根据必须是非形式的。你们看到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些相当晦涩的思考,努力去理解吧。
7 非形式(非对称)的根据
L. Lawlor:在上周北京大学的讲座上,我讲了一个笑话:如果你们知道《反俄狄浦斯》、读过一点德勒兹的思想,你会发现当他和加塔利合作时总是在写“流(fluids)”。你第一次读《反俄狄浦斯》的时候会想,“这两个家伙简直是疯掉了,他们在说些什么,天呐,至少给我一点我能理解的东西吧!流?什么流?好吧,至少我知道流体没有形状。”所以,我讲了这个笑话,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这确实是在阅读德勒兹的思想时非常自然的过程。在六十年代末他独立写作的那段时间,他感兴趣的是什么是非形式的。
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关于对称和非对称的图示了。不对称的形式不正确、不平衡,你甚至可以说“我不觉得这有任何形式可言。”如果你们了解过的话可以想想看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他把颜料甩到画布上,非常大的画布,巨大的画布。当你看那些画的时候,如果你接受过传统的绘画训练,你可能会觉得这甚至完全不是艺术。但它是个值得欣赏的作品,你只要看一看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在几秒钟之内你就能看到其中的智慧。但你们可以看见这有多难、我们怎样才能谈论没有形式的东西,显然语言是有形式的。德勒兹很少写语言哲学,但他偶尔还是会写一些,以通常以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方式写作。
我们稍微离题来讨论一下非理性的语言。你在阅读加塔利如何谈论语言的时候,会注意到一种必须从口吃的角度来理解的语言。你们知道这种现象指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完全理解到了。我认为人们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口吃是一种大脑健康方面的问题。但你们亲眼看到过有人口吃,对吧?“啊哦哦哦……”如果你看见过任何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看着他们这样都难受。他们永远到不了句子的结尾。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正是关于语言,与语言非常接近,而不完全是生理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他想要努力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你们可能会用眼睛去看,但是眼睛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我们得要听到动词。你们听到的东西大概是“哦哦哦哦”,对吧?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它和语言非常接近,但还不是语言。所以说,这里是一种非对称。你可能都不需要哲学思考就会想到这个口吃者的表达十分混乱(“表达混沌”)(expressing chaos)。他一边口吃一边想说些什么,而我听到的只有噪音,但是他对要表达的东西确有一些形象(image)。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谈论没有形式的东西。
好了,我接下来会用条理更清晰的方式说一遍。德勒兹会说,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现在都是某种重叠起来的状态。口吃就如同二十世纪的非对称抽象绘画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对背景或者深度的经验。
我们再次回到循环论证这个主要论题,它被称作循环是因为:你该怎么逃离它?你看,我需要再“解释”它一遍。我们在英语日常语言里常常使用“解释”(explain)这个词语,许多时候人们说,我们需要解释我们对他们说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理解其充足理由。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解释。随后你尝试去解释这个事物,而你的解释会和你第一次说出这个事物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吧?否则就陷入了“相似关系”。德勒兹在这种根据的相似关系中做出了突破,说出了与被赋予根据者完全不相似的东西。赋予根据一个形式的东西必须是非-形式(a-form, non-form)。
我再说一件事。胡塞尔有一个关于被给予性的“一切原则的原则”,但德勒兹不把这个东西叫做原则,虽然他的确有一些和“一切原则的原则”很相似的东西。这对我们理解德勒兹的思想非常有趣和重要。你随意打开一本书,这本(《差异与重复》)和下一本书、《意义的逻辑》里,他会说根据永远不能和被赋予根据者相似,永远不能。我们就是通过跳出相似关系来跳出这个循环论证。
你们看到这些问题了吗?现在看起来又是怎么样的?你们知道如何从这些问题里跳出来了吗?似乎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经常落入这种循环之中。所以,你们可以在吃午饭的时候测试一下,听听你们的朋友如何解释事物。必须承认我自己在日常语言中也常犯这种错误。解释几乎总是看起来和被解释的东西相似,但德勒兹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哲学思考。根据决不能与被赋予根据者相似。
8 不依赖相似关系的发生
马浩然: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根据必须与它赋予根据的东西完全不同,但如何处理它与康德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呢?康德认为在经验中有一些先验的成分。我也相信根据与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之间有某些关联。这里肯定有某些关联,如果这些关联不是相似关系,那它们是什么?
L. Lawlor:这是一个对德勒兹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德勒兹同样也使用康德的术语,但康德是他重要的对手,实际上他想要批判康德的批判哲学。他在康德哲学里抱怨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词语:康德的哲学只是“结构的”。时空的结构和范畴相似,比如因果范畴。但德勒兹想要给出的不是结构。
此时,1960年代,对法国哲学来说这样一个时刻:我所知道的所有法国哲学家都想要讨论“发生”而不是“结构”。非形式的东西就是一个发生源,把它称作“起源”也许更加合适,进而才是“根据”。但德勒兹不太常用“起源”这个词,这更多是一个现象学词语,海德格尔会用得很多,即Ursprung(起源、本源)这个词。再一次,要注意的是你必须发生性地、生产性地思考这个关联,而不是一种结构性关联。所以,这个基底之物、大洋深处之物,是发生性的。它不与它产生的东西具有相同结构,它们并不相似。
我应该举一个例子,它在我给你们的文字材料的第一页和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有。如果你想要认真地阅读德勒兹,你总是会想要关注第一页、每一章的第一页。在许多译本里,可能过了几段就会有一个间隔,然后重新开始算页数,但是有时候在法文本里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关注前一两页吧,尤其是《差异与重复》,如果理解了前两页,那你就已经掌握这一章的内容。前两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浓缩了所有会用到的概念。
这个我要用到的例子来自《差异与重复》第一章前两页。德勒兹谈到了闪电如何击中那些树,谈到了闪电从天上降落的过程。他有一个海渊的意象,这还有一个天空的意向。但我会说我更喜欢这个我后来给你们的天空的意象,因为德勒兹说过闪电来自其“基底”。我不知道这个词(le fond)的中文是什么,在英语里是background。它是一个有关根据的词,有关根据的词在英语里要么是ground,要么是background,对吧?——从基底中浮现,而不与基底分离。
你们肯定都见过天上的闪电,尤其是在太阳已经下山之后的傍晚,你们仍然能看见天边的云彩。你们能看见那些云的形状,对吧?闪电就从中出现。德勒兹也说,是这样,但闪电从未离开它的基底,它自身行分化(differentiates itself)而不离开自身。
让闪电在云层中产生的是电荷,一正一负,云层中的正负电荷相互作用或者说就是撞上彼此。这里闪电就产生自电荷的差异。电荷的差异。 我们看到了“闪电簇”(lightning bolt),bolt表示它箭簇般的形状。我强调(德勒兹自己也强调)闪电这个例子的理由是,他认为我们仍需要通过闪电的发生源来理解闪电究竟是什么。但他同时也在担心这个例子不够好,他担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被产生出来了、是什么现实之物与其源头分离?
我们再回到这个循环论证的问题上来:根据是什么样的?首先,它是一个发生性的本原;第二,其中包含了差异;第三,我们有正负电荷——我们可以称其为“量”。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办法去谈论这个看起来没有形式的东西。比如我们可能会用“量”来思考它,对吧?我们必须用“差异”去思考它,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重复,对吧?我们正在发现谈论它的办法。
9 德勒兹那里的先验与繁复体
马浩然:我可以把“根据”理解成康德那里的先验质料(transcendental matter)或是纯粹杂多(pure manifold)吗?
L. Lawlor:纵观德勒兹的学术生涯,在六十年代他曾用过“先验”这个词来描述他自己的哲学。但我会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只不过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他说的那种根据(foundation)。所以我会说它是先验的:基底中的电荷正负差异是一种先验的基底;同时,再一次强调,这种先验的基底不与其产生的东西具有相似关系。
而“纯粹杂多”这个词,一种翻译这个德语词的方式可以是“繁复体”(multiplicity)而不是“杂多”(manifold)。这基本上是同一个词,因为multiplicity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pli-,在拉丁语中的含义就是“fold”(折叠、包裹)。
刘任翔:德语中这个词是Mannigfaltigkeit。
L. Lawlor:是的。它就相当于multi-folded(包含-多)。这也是另一种描绘德勒兹思想的方法:非常简单地说,他是一个“繁复体/多样性”(multiplicity)的哲学家。所以我们还可以说,他认为繁复体要先于其形式。
10 前-形式的“多”
L. Lawlor: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差异与重复》的第一章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前十页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让我感到十分抱歉的是,我不太了解亚里士多德在东亚的地位,但在西方,他的确是第一个尝试给动物归类的西方思想家。他发展了种属的观念。比如这个工作给众多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一个统称,陆生动物;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种类。大象是一个种,兔子是另一个,它们共同所属的属则可以是“走路而不游泳的动物”。目前为止还没错,但你们可以看到其中的问题。2500年后,我们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进行归类——我们首先看到属然后在其中看到很多特殊的种,你可以把它应用于,比如,一棵树。先有属这个基本的形式,这个形式被实例化(instantiated)到一些不那么基础的形式(种)中,这些形式又被实例化,这是一个从普遍下降到特殊的过程。
但德勒兹想要把它翻转过来:种属从动物的多样性(multiplicity)中产生出来。这种前-形式的多(multiplicity)还不是形式的,前-形式的东西先于形式的。这个内容可能没有一开始那么让人兴奋,我想,这是哲学很技术化的一面,但你们会理解到去翻转这个思维方式是解放性的。
让我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会思考性别(gender)问题,性别在现在的英语世界是个非常大的议题。但在其他常见的文化中,包括亚洲的,我会说这些文化里有许多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形式,其成员也会被要求达到这些标准形式,对吧?但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些形式其实是从多样性中产生的。所以通过说明多样性里有许多不能被框定在形式中的部分、多样性要先于形式,我们就能够批判这些形式。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是通过选择多样性中的一些特定特征,然后把它们塑造成普遍形式来形成的。但显然还有其他的特征没被算进来。
在德勒兹这里,多样性是优先的,然后才有属。话语是被建构起来的,就如德里达所说,它能够被解构。我们能够解构属,来知悉多样性真正的样子。在英语里,对一个行为奇怪的人你可能会说他是个deviant(变态),因为它“违背”(deviates from)了标准。多样性是我们生产所有普遍形式的生产源,但那些普遍形式全都背叛了多样性的真理。
这就是我想要让这种思考变得更当代的理由:我会说,在美国,尤其是种族主义这个大问题上,近十年来情况其实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思维方式基本上被限制在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中,但如果能够理解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发现它是一种解放性力量。我们已经从很理论化的观念进展到了实践的观念。德勒兹不会用“解构”这个无聊的词,在80年代,他用的是“摧毁”(destroy),显然和解构的意思差不多。
11 无法化约的真理:理论和实践的层面
叶家敏(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我有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尼采,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某种哲学无非是某种身体状态的表征”,所以我想知道德勒兹如何解释“疾病”是如何产生的。
L. Lawlor:显然,混沌(chaos)这个词是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在其写作生涯的晚期,尼采曾说过这样一个短小的句子,他说“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信条就是混沌。他的意思是混沌就是那回归的、总是回归的东西。但为了解释那个发生源,我会给出另一个图式:德勒兹以数学的方式来解释它。你们可能一下子没法反应过来。数学显然是我们思考的最形式化的方式,我们在此使用等式、公式等等。德勒兹寻求数学的解释。
通过这个图式我们看到,在充足理由被设想的传统方式中、在西方哲学中,被设想的那个根据总就是上帝。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哲学都总是保有神学的背景,尤其是从公元300年到1500年的这段时间,哲学总是诉诸上帝。早至从柏拉图开始,这个上帝就常常被设想为一个“数学家”。我想再提一次达·芬奇,他实际上是通过制定人脸的比例来定义属于人脸的美丽。那么这里则是上帝这个数学家创造了人脸与属于它的美丽——上帝必须是一个数学家,因为祂明白一切的比例。
但德勒兹改写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数学家上帝其实并不擅长数学,并不知道该怎么创造。好吧,我也很不擅长数学。如果你们读过《差异与重复》或了解德勒兹,就会知道他求助于微分学来解释发生。而我从来没上过微积分课程,也总是很害怕它,所以我就直接开始研究德勒兹了。我有12本关于微积分的书,每一本我都大概读了30页就放弃了,因为之后的内容我再也看不懂了。所以这个数学不好的上帝就有点像我吧!
总之让我们回到这个图式:上帝创造了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创世神话。但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是个差劲的数学家,祂就按照一个无法约分的比例创造了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例子:几何学中的π。它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有时被表示为22/7。从195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对π的求解,而π则事实上不可解。它永远不会结束于一个整数,而是生产出无尽的小数。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数学是一个对世界的比喻。世界如同一个无理数一般被生产出来。当德勒兹讲述这个创世的故事时,他会把这个世界称为无尽的余数,如同无理数中无尽的小数一样。π大概是3.1415926,这是“求解”无理数的一种方式,在英语里我们会说这是“取整”(向上取整(round up)或向下取整(round down))。
比如,当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它的价格是3.89,你可以告诉那人这是4元,这是可以的,他给你向上取整了。或者你可以说“我3.80拿了”,这个卖你东西的商人说“可以的,我不在乎那9分钱”。所以我们有这种向上取整的方法,把数字变得更接近整数,3.9或是4元。而我们向下取整的话,就会有3元。这个卖东西的人今天可能特别慷慨,说“没事的我只收3块”。所以你们能够看到,问题出在有关世界的真理上——这个世界是按照作为无理数的比例创造的,那么显然把事物取整就是“不忠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一切联系起来了。“取整”这个做法就像是说:“考虑到所有存在的事物的多样性,这就有太多差异了,就像是无理数中的小数一样。无限的多样性。我不打算考虑它们,我要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普遍形式、一个整数。”
回过头来,你们可以听到我强调了“真理”这个词。如果你们仔细地阅读《差异与重复》,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真理的内容,可能就出现了三四次。但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德勒兹谈到了某些事物的永恒的真理。你们能想到π吗?我的意思是,显然,如果你们已经发现了π的解,那么只要你发现了一次,直到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往后过十代人、过一千年,π的值仍然为真。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将永远保持为那个数字,永远也不会变成整数。德勒兹总是会谈及永恒的真理,但显然是如同那些无尽的小数一样的真理。如果你将其取整,那么结果就与真理不相即、就实际上是错的。
但同时,它还有伦理的一面:如果某人对真理进行取整,德勒兹就会说这是“不道德的”(unethical),因为这就是要只以普遍形式对待人、以等级制对待人。你们可以在这种行为中看到那些美的形式、对称性,它们都可能强加在我们头上,直到我们能看到那些非常非常恶劣的、甚至是道德上恶劣的对称形式。我们太过于“非对称”——想想所有人、想想我们的举止,没有人能变得那么“对称”。但人们可能会说你不正常、你做的事不正确,你也可能和你的孩子说,“我觉得你的方向错了,你这样走下去最后会惹上麻烦”。通常是家长和他们青春期的孩子这么说,他们可能过渡饮酒或是滥用药物,比如,如果我酗酒嗑药,那我从青年开始就“不正常”。
你们可以看到理论哲学真的和实践哲学没有多远。我们回到无理数、依据不可约分的比值创造的世界,然后你可能想要将其取整,然后你突然想道,“等等,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这小数的一部分,那如果将其取整的话,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于此你开始考虑到,这意味着“我也将被取整,进而被置于一套等级制中,而我可能处于这套等级制的底部,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好位置,因为这意味着我可能会遭受剥削、不会被好好对待”。你可以看到其中所有的政治意涵,比如贫民窟、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所有这些结果听起来都不好接受。所有这些都是“把小数取整”的后果。你们可以看见理论与实践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12 德勒兹伦理学中的主体性
杜昕蕤:我想更多了解一下这个权力结构、等级制结构中的主体性,因为主体性对有关德勒兹的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但我想知道德勒兹那里是否真的有主体性这回事。
L. Lawlor:好的,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德勒兹,就和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一样,对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和加塔利合写那些著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德勒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中期的1910年代说,意识是无意识的一种症状。德勒兹赞同这一点。但意识是症状,是就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而言的。德勒兹说症状是可以被治愈的,随后我们会拥有一种不同的意识。在这些早期著作、我谈到的这些理论化著作中,无意识总是被批判,因为德勒兹认为它是定义了主体的那些习惯性形式。
但在他随后与加塔利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在研究生课程中教学《千高原》的时候我经常强调的,在这本书论语言的那章里,德勒兹和加塔利会说“少数意识”(minor consciousness)。他们事实上发展了“少数”(minority)这个概念。这也是他们谈及“口吃”的地方,少数其实就是一种多样性(multiplicity),而少数意识就是繁复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multiplicity),而非普遍形式。我们日常的意识通常是被所属的文化决定的,是一种标准形式与等级制的意识。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能够完全逃脱这些限制。当你们离开这个房间时,你们马上又会回到那些等级制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抵抗的,似乎就是不可能打破这些思维方式。但是德勒兹仍然敦促我们去做。我会认为意识在他的这些论述中起到了一个次要的作用,它也必须是一种变形的意识,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意识、不是笛卡尔式的意识。
杜昕蕤:不像笛卡尔?
L. Lawlor:是的,他总是批判“我思”。这可能有些离题了,但是——笛卡尔式我思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思想,而在于这个我思,它对应着与不同经验方式相协调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当我“思考”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也是我在“回忆”它、“想象”它。如果语言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话,我还能“谈论”它。所以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所有不同的经验方式都是同一回事。笛卡尔对“我思”的设想就也可以是“我想象”、“我回忆”、甚至“我说”。但德勒兹认为这些职能(faculties)中的每一个都只对应着一类特定的对象,它们决不相同。这是个相当激进的想法。这就是说,当我回忆一个对象时,这不同于我想象一个对象、不同于我谈论一个对象。但从笛卡尔到康德,它们思考的是各职能之间的协调,所以在这些职能之间必须有一些相通的东西(common sense)。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批判笛卡尔的我思概念。
但就德勒兹的思想而言,如果任何人想要了解他的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次发问都关乎思想——我们究竟如何思想?如果你们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德勒兹、对他的思想感到激动,那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一种关于思想的新的思考方式。
13 “清空”时间:过去与未来的去当下化(de-presentification)
华宇思(哈佛大学神学院硕士生,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您适才提到,在德勒兹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的瞬间不是一个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存在的时刻或当下的时刻,而具有某种生成性。海德格尔也认为时间是绽出,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聚合为一体的存在。我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与德勒兹的时间概念根本上的不同在何处?
L. Lawlor:这是一个体量很大的问题。我不确定绽出是否与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有关。
德勒兹描述时间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思路很接近,他们都认为当下的时刻总是在流逝。胡塞尔说活生生的当下中蕴含着前摄与滞留,人们可以预期、记忆,而事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流经意识。所以德勒兹说没有严格的现在,和海德格尔说没有严格的现在时的意思是一样的:当下为绽出所定义,德勒兹也认为未来与过去定义了现在。
但是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的术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代之后,他开始讨论大地、神,甚至到五十年代。我知道有学者理解这一转变的缘由;但即便你读了他后期的很多文本,你还是会想,他究竟在说什么?无论如何,德勒兹确实非常关注时间被依照当下而定义(defined in terms of the present)的问题。
我们习惯的思考方式是——我一直在使用“习惯的”(habitual)一词,因为德勒兹实际上在批判习惯——我有一段记忆,那是过去,但我也有对当下所经历之事的记忆;或者,我可以预期未来,但当我想象未来之时,它其实是一个“将来之当下”(future present)。这意味着,过去和未来并未被真正理解为它们本身,而被理解为当下的变体。德勒兹、胡塞尔以及《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都希望突破这种只把时间定义为“不同类型的当下”的思维方式。
就此,德勒兹谈到了“时间的空形式”(the empty form of time)——如果你去查关于德勒兹的时间概念的研究,有不同语言的两千多篇文章,二三十本书,都尝试讨论“时间的空形式”;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很重要的问题,空(empty)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时间并非由当下的内容构成。这很可能是受柏格森的影响。在《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探讨了“纯粹过去”(pure past),这是一个先于所有“过去了的当下”(past presents)的意象而存在的过去。德勒兹对剥离过去的具体内容,视过去为过去本身而非“曾是当下”(was present)的东西这一理念深感兴趣。视过去为过去,意味着抽象掉了所有内容,将过去作为过去本身对待。未来也是一样,你需要“清空”它。彻底“清空”所有的“过去了的当下”,才能得到一个只是过去(或者只是当下、只是未来)的“时间的空形式”。
我不确定这如何和海德格尔相关联,很明显,“时间的空形式”和海德格尔自己的术语相去甚远。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在二者间搭建桥梁,来让“时间的空形式”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对话。
华宇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德勒兹吗——过去和未来都是“空的”,时间是不同的诸当下?
L. Lawlor:不,他是在批判“时间是不同的诸当下”的观点。时间的“空”表示内容的清空——这源于他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时间的内容是我们的日常经验,比如“你今天活着”。你记得2023年在北京参加Lawlor的研讨会时,他以自己“喝酒太多”开玩笑,这场研讨会你只记住了这一个片段——这就是彼刻正在经历的“当下”。这将被界定为一个“过去了的当下”。德勒兹会说:不,这是将过去还原为当下,未来也还原为当下;他主张将过去和未来都无内容地、如其所是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清空了记忆,清空了预期;是这个逻辑。
华宇思:我需要琢磨一下。
L. Lawlor:这与海德格尔有关。海德格尔像德勒兹一样强调未来的优先性;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里,海德格尔谈到“向死存在”,向死存在就是向“无”存在。在1929年的短文《形而上学是什么?》里,他谈到“畏”(Angst)是一种我们面向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与无(the nothing / das Nichts)有关。他把这个词变成名词。但是无就是无,没有内容。
这与德勒兹的想法很像——我们思考未来和死亡时,要把其中的“将来之当下”(future presents)清空。用英语表述其实很奇怪。他不会把“当下”(present)这个词复数化,除非在说“礼物”(presents)。但我正在谈论的是时间的部分;我们一般将过去和未来视作一系列的当下。你今天离开的时候,会想今天早上如何如何;一年之后,你会想,一年之前你如何如何;然后是十年,等等。对当下这场讲座中的体验,你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每当你提到“当下”时,德勒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海德格尔,会说:不,你需要抛开这些内容去构想过去,也需要抛开这些内容去理解未来。海德格尔的语言是,未来是“无”,不是东西(no thing)——这是我们当下无法体验的。无论好坏,我们都没有其他方式去思考死亡。我这样说是否清楚呢?
华宇思:我明白了。
14 时间的无限与生成
刘任翔:或许我们该回到“一切原则之原则”:基础绝不能与其所奠基之物相似。我在尝试理解德勒兹此处的论证——假如这里有论证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假如基础确实和它所奠基之物相似,那么我们必然要寻找更深的基础;因为它们彼此相似,我们就并没有得到关于被奠基之物更深层次的解释;但这只会导致无穷后退。在这个链条上,一个与此物相似、为此物奠基的基础总是又被另一个相似物奠基着。
这让我联想到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批判。我们试图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原因(ground,即根据、基础),并认为那是一种高于、先于我们的存在者。但在这个链条上,我们就只能找到与我们相似的存在者,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像”我们的存在者(beings like us)。最终这个推论会以一个“大写的存在者”(big being)结束——也就是论证中的上帝。沿着这条路径,等级就会产生:我们拥有了一条“存在巨链”,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以和“大写的存在者”的相似程度之深浅而被定义、定位。
但是,假如德勒兹想要去打破这一“相似性链条”——它在传统哲学中也被称为 “存在的类比”(analogy of being)——那么他就需要给我们一个存在(而不是存在者)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将以“存在者是被存在、而不是被一个更进一步的存在者所奠基”的思路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是如何被奠基的。这是否说得通呢?
L. Lawlor:可以这样理解。即便这方面的证据不多,但我认为德勒兹从海德格尔的想法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差异”说明,存在绝不能用存在者来定义,这也包括上帝。但关于无穷后退,另一种描述德勒兹思想的方式——虽然也引出了很多费解的点——是他是一个研究“无限”的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要避免无穷后退,但德勒兹反对这一做法。如果你回避无穷,你实际上再一次未忠诚于对时间的真正体验。因为当你清空时间的内容,会发现过去没有开端,没有初始的“当下”;未来也没有终极的“当下”。
这恰恰是一种解放,因为——如你所说,存在的类比让上帝成为第一推动者,而上帝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我们以与“完美”的关系为尺度被衡量,这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属”的问题。上帝是“所有属的属”,而人类只是上帝的复制品——甚至是拙劣的复制品,海里的鱼是上帝更加拙劣的复制品,石头则离上帝更远。所以等级(hierarchy)是从一种特定的对存在的理解中形成的。
但等级秩序也同样可以源于对时间的理解。我们习惯性地将时间设想为有一个起点。大多数文化都有类似的观念:存在某种“天堂”(paradise)——人类从那里堕落,在尘世经受苦难,最终回归天堂。时间事实上被构想为一个圆:从这里开始,经历苦难,最终回到这里。但这本质上设定了某种作为准绳的“当下”。至少在西方的《圣经》中可以看到这种构想:开篇是对“天堂”的描述——它美好、丰饶、食物充裕、没有痛苦,然后我们堕落了,我们在地球上度过悲惨的生活。假如我们行善,最后就能回到起点。
这种理论意味着起点是某种“当下”,终点也是某种“当下”;但当你清空时间的内容,时间则无始无终,究极无限。如果你用无穷倒退去描述,我认为是行得通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德勒兹是一个关于“无限”的思想家。任翔说这里面有伦理思考的部分,他用“等级”一词表述得很清楚,我们是参照着完美的形象被衡量的。
这就是为什么以“时间的空形式”去理解时间是重要的,它使我们从这种衡量中得以解放。刚才任翔也提到了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如果你们读我的文本,会发现我特意使用了“关于时间的宇宙论证明”(a cosmological argument about time)这个表述,它本质上是一个“反上帝”的论证。
过去几年里我多次谈论关于时间的这些观点,但通常是在已经喜欢德勒兹的人面前,所以我很少受到批评;但在北大做讲座时我受到一些质疑……总之,核心论点是:经验性的时间(empirical time)是无限的。
德勒兹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经历的时间是无限的。时间似乎可以向过去越来越远、无限回溯,我不能想象它曾是什么;时间也可以向着未来无限延伸,我也不能想象它将是什么。德勒兹认为,时间是无限的,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你听到了这个论证:假如世界有一个完美的“平衡时刻”(an equilibrium moment),那么由于过去是无限的,世界一定早就变成了这种完美的状态。如果这一平衡时刻“需要时间”来到达——我用“平衡”来指称那种无理数的比例,无法被化约的状态——那么在无限的过去里,它早该到达那个完美的平衡点了。但宇宙至今仍在“生成”(becoming)。这说明,宇宙并非在“生成”某个既定的东西。就像你想要达到某个级别、成为某个东西,这需要时间;但如果你拥有无限的时间,你就会想:“我早该在很久之前就达成目标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过去的时间是无限的,且宇宙在“生成”某个完美的东西,那么它早该在很久以前就达成了。所以,宇宙根本不曾试图一劳永逸地达成某种完美的形态。但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当我们观察宇宙时,它仍在运动,仍在生成。
所以,宇宙并未在“生成”某个特定的东西。我在书面文本中还补充了论证的另一部分:如果你把时间或生成视为“某物的生成”,你实际上并未真正将“生成”或“时间”如其本身所是地对待,而只是把它简化为某种恒常(permanent)之物。你根本没有真正思考“生成”,只是把“生成”当作某种恒常之物或“当下”的变奏。也就是说,你并未从时间与生成的视角思考时间与生成。
总结一下论证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们时间经验的描述,第二部分则是更现象学式的对经验的描述。
15 存在的单义性:超越等级与界限
刘任翔:您适才提到宇宙的生成特征。根据某种特定的宇宙观或历史–神学观,存在着一个“平衡时刻”。这让我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论述。他将时间定义为趋向完美状态的运动的计数,这一运动总是参照着完美状态被定义的。这意味着,对德勒兹而言,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生成”并非真的生成。
L. Lawlor:正是如此。之前的讨论里,我们提到德勒兹是关注潜能的哲学家,但那并非目的论意义上的潜能。生成没有一个“隐德来希”(ἐντελέχεια)——希腊语中“生成将终结于此的目的”。生成并不在某处终结,它只是单纯的“生成”。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想起来却很困难,因为我们平常不是这样思考的。比如在大学里,你总想成为某种人、达成某个目标,成为哲学家、作家、化学家等等。无论如何,你总想成为些“什么”。你会认为这是你的潜能所在,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奋斗。但是问题在于,德勒兹所说的潜能没有单一的目标,也没有单一的朝向;它总是有很多的可能。
时间原因,我们迅速讨论几个别的问题。
第一,德勒兹的存在论是什么?任翔适才提到了存在的类比。当德勒兹谈论存在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存在的类比理论,而是“存在的单义性”(univocity of being)。如果用拉丁语做解,“uni”是“一”,“vocity”则是“声音”(voce)的变体。在存在的类比理论看来,上帝是完美之物,除它之外还有各类的存在者。我们可以将这些存在者分组——人类、高智商的动物(如猿类或大猩猩)、智商较低的动物(比如熊)、智商更低的动物(比如鱼)、智商还要更低的动物(比如变形虫、微生物),一直到无生命物质。在存在的类比中,你会说每一组存在者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这每一个意义都最终以类比的方式关联于上帝的存在。你会发现这违背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原则——上帝作为一个存在者,被当作存在本身的意义,而存在的多重意义在不同程度上相似于(resemble)这个单一的存在意义。
你可能会问,德勒兹支持复多性(multiplicity),支持存在具有多重意义,以上所述不就是他的立场吗?不。上述复数性意味着参照一个单一的存在意义建立等级制(hierarchy),这个单一意义将在其它任何一种存在意义中复现。
与此相对的“存在的单义性”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提到德勒兹支持复多性,这毫无疑问。而存在的单义性是“一个声音”的意思,看上去是同一个意义统摄了所有的存在者(one meaning for all the beings)。但这里确切来说是,这个意义是属于每个存在者的(one meaning of all the beings),或者换句话说,它是所有差异共享的意义(one meaning for all the differences)。这里发生了一个关键的转变:存在的单义性意味着以同一种存在之意义,无分贵贱地理解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无论是无机物还是人类。所有存在者都拥有相同的存在意义,只是在拥有的度(degree)上不同。这里的“度”需要以不同于等级制的方式理解。
德勒兹想用“单义性”(univocity)这个和声音(voice)有关的词传达的是:存在是“被言说”(is said)的;学界很少有人探究声音或者“被言说”是什么意思,但存在和言说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去言说存在,但不是言说上帝的存在,而是言说诸存在者的存在。前者指向那个完美的意义,而后者则指向意义的弥散(dispersion)。后者导向众意义的平等;而前者导向等级制和不平等——用完美衡量一切,我们就会认为,某一些存在者比另一些更有存在的意义。德勒兹认为,我们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拥有的方式不同(并非类比)。同时你也不能认为存在是强加于存在者之上的,它只是在各种存在者那里被言说(said of beings),是我们这些存在者存在着(we be)。
存在的单义性不同于对存在的衡量。对德勒兹来说,那是所有“喧嚣”(clamor)所由来的那一个声音(one voice)。你站在街头,汽笛长鸣、手机通话、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这就是“喧嚣”;而所有这些喧嚣来自于一个声音。在喧嚣中,诚然是有许多存在者在各行其是。德勒兹试图用“潜能”(potentiality)阐释这一点:每个存在者——由于它并不在等级制的束缚中、不为某种框架所缚,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可以做任何它可能做的事情。想想斯宾诺莎,只有通过存在的单义性,你才能知道你的身体能成就什么、心灵能抵达何处。
德勒兹说抵达你能力的极限,这“极限”并不意味着终止,而是某种可被超越之物。以日常为例,你或许认为在班上名列前茅就算达成目标、到达了自己的极限。从存在单义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极限之外,还有更多你可以去做的事。对德勒兹来说,没有完全的肯定性(complete positivity),你所做的一切都并非对某种匮乏的填补。当达到了所能的极限,你还将走得更远。
这听起来像我们总给孩子灌输的鸡汤——尽你所能、做最好的自己。但这儿说得显然更多、更激进,做到最好并不意味着全部,总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去尝试。你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运用自己的身体,突破迄今的程式。思想的潜能和力量也一样,真正的思考意味着去思考你本不能思考之物。
我再补充关于“度”(degree)的一些看法。存在的单义性——“一个声音”这个概念中,德勒兹把这个单一的意义构想为动词,一个不定式动词。不定式的动词形式先于动词所有特定时态、特定使用情景,是动词被具体使用之前的原初形式。所以存在的单一意义(the one meaning of being)就是“去存在”(to be),这也是我刚刚说“we be”的缘由——而我们中的每个人则是不定式的变位(conjugated)。
以语言学习为例,我小时候上过许多英语语法课,毫无困难,因为我早已知道如何说话。不懂语法时态,我也知道“we’re going to go somewhere in the future”是什么意思。变格有许多规则,它是原本不定式的动词实际被运用的方式。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以变位了(conjugated)的方式存在,而我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存在是单义的——“去存在”(to be)。“to be”是不确定、有变位的,而上帝是拥有无限理性、至善至美、完满无缺的。存在所有的、唯一的意义就是“to be”——先于所有的变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你都是不定式的变位,没有优劣之分。
16 强度;质的派生地位
L. Lawlor: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强度”(intensity)。要理解德勒兹,这个概念是绕不过去的,他几乎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谈到强度。
强度是一个关于量(quantity)的概念。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也称之为“度”(degree)。光可以更亮或更暗,光线充足或者光线不足。你可能想量化这种度,但德勒兹希望我们以无限的方式(infinitely)理解强度,把它理解为无理数的无穷序列。
他用白墙——一个来自中世纪哲学的意象来阐释。你可以借助外在(external differences)和内在差异(internal differences)两种差异来区分白墙。在白墙上涂写,在外部施加痕迹,这在它本身之外,是外部差异;除此,白墙自身还能区分出不同的明暗色调(shades),这是内部差异。
在现代制造业中,产品往往只有一种色调,多色调的产品需要制作者付出额外的努力。但百年前的白墙却能自然地呈现丰富的明暗之色,这些细微的明暗差异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内在差异。
惯常的思考方式会问,明暗?什么的明暗(shades of what)?最直接的答案是白色,即白的质(quality)。人们几乎不由自主地会以“of”(…的…)来结束这个问题:明暗是白色的明暗,是白色的质的明暗。但实际上,是明暗色在先,白色、白色的质而后派生。想想这个转变,法国哲学总是在颠覆等级,将底层概念置于顶端。
要理解这种反转——明暗在先,质在后,你要将明暗理解为动词“去白”(to white)的变格。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英语表达,一般只有诗歌会把“白色”当动词使用。但德勒兹会说,一切的质,或圆,或方,或不规则,拥有各不相同、五彩斑斓的奇异色彩,它们实际上是“去圆”(to round)、“去高”(to be tall)、“去低”(to be short)、“去绿”(to green)不同程度的表现。
以身高为例,这个房间里大家身高各不相同。你或许觉得“高”就是更好的、更趋向于完美的形态,谁长得矮谁就不好看。但我小时候曾为此苦恼,比同龄的孩子高很多常常让我很尴尬;但大家现在都长高了,我倒变成了小个子。你也可能认为矮一些更好,很容易融入人群、藏起来不会被发现,这是高个子做不到的。这里面掺杂了很多伦理层面的评估。
所以说,正是不定式最终衍生了所有的相关变格。这些变格中的每一个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彼此是平等的。你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说德勒兹哲学偏好不等(inequality)、无理数比例吗?怎么现在却成了平等学说——而且还认为万物在存在上具有单义性?这如何可能?
让我们回到一切原则的原则——奠基者决不能与被奠基者相似。如果被奠基者(the grounded)是一种形式(a form),奠基者(the ground)就必须是“非形式的”(aformal)。但我们又说时间的空“形式”,这是怎么回事?但这正是德勒兹的想法,形式是有内容的,但时间的空形式是没有内容的。无论形式是什么——我们之前简单提到了过去和未来,它们都不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事物;否则它们就被当下的形式定义了。存在的单义性学说赋予我们的平等实际上是允许我们每个人成为我们各自所是的“度”(to be the degree we are)。假如你是白色,那就是去成为你所能是的那个色调的白色。像要成为(特定而无高下的)明暗一样,像动词“去明暗”(to shade)的变格一样,奔赴你所能是的极限。
有些学者认为德勒兹是形式主义者(formalist),有些认为他是反形式主义者(anti-formalist)。德勒兹于1995年去世,但三十年前大家就在争论他的政治哲学是民主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甚至有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因为法国哲学家都对马克思怀有敬意,马克思是他们或隐或显的思想背景。德勒兹维护民主制、支持平等吗?还是说他维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这种哲学中“平等”价值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人们应共同生活、相互照料?
德勒兹追求的是容许差异的平等。平等并不必然泯灭差别,而是即便我们在强力(power)、强度上相异,仍能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彼此。Power和intensity这两个词都是德勒兹常用的概念,几乎是同义词。
刘任翔:这里是否存在着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张力——平等是说所有人可以无分贵贱地发展自身的潜能,不平等是说每个人的现实轨迹有绝对差异?或者说,人们在各方面都不同,不具有可比性,而他们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平等的?
L. Lawlor:是的,人们是不可比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我用我的身体能做的事和你用你的身体能做的事截然不同。举一个笼统的例子,可能你在数学上比我有天赋,而我比你更擅长语言和写作,但这哪一个也不能说明我们谁比谁更好。我能做的事是只属于我的(mine),不可与他人比较的,它只表示不定式“去写”、“去做数学”的度。这里存在一种“共通性”(commonality),但不是:“质的共通性”(commonality for quality)。注意听这几个词——“equality”、“quality”、“inequality”,白色的“质”导向等级秩序,德勒兹在这个意义上是“反质的”(anti-quality)。在他那里,质总是派生的。
17 “自取灭亡”的强度与“危险”的哲学
L. Lawlor:让我们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观点收尾。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第五章——围绕“强度”概念展开,强度似乎一头扎向自杀,径直向前。他援引了熵理论,熵理论认为,恒星终将燃尽,万物终将冷却,整个宇宙将一去不回地走向寂灭。太阳是光和热的来源,强度的源头,(而它终将熄灭);所以从宇宙论视角来看,强度自其本性上就将自取灭亡。
这启发我们思考:是什么驱使你不断地超越极限、你又终将抵达何处?一个运动员拥有永不餍足的野心,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极限,结局未必尽如人意。日日写作,不眠不休(学生们赶DDL、准备期末考试,这类体验肯定不少),最终很可能会进医院。所以在读德勒兹的时候,你还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词:“危险”(danger)、“风险”(risk)。德勒兹深知自己思想的危险性——促使你触摸到自身极限、鼓励你去超越它,这未必有好下场,很可能是一条冥府之路。所以即便在这本极其理论、枯燥的书里(里面微积分的部分让我非常头大),“危险”这个词也出现了五六次,之后与加塔利的合著中则出现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