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时间:2022年6月2日
领读学者:尤西林
录音整理:张敏、严嘉年、曲经纬、刘任翔
字数总计:12000
完读时间:1小时6分钟
1 方法论的澄清
尤西林:时间的话题首先并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话题,这是一个生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问题。我们须臾不可能离开时间,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自然的时间状态。这种时间的状态,是生命本身的要求,它可以起源于自然。所以我把题目定位在生命这个起点上,就是希望说明我们讨论的话题具有普遍性。然而,时间问题也需要在更广阔的历史中,使用现象学的方式进行描述。
奥古斯丁说,“如果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反而不知道了。”这句话从知识论的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不可以把时间作为一种通常的知识论专题来加以研究。但是他后边说:“不问我的时候,我倒是在时间之中。”好像他知道时间,其实不然。
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大部分的时间中,并不自觉意识到时间,这并不意味着时间对我们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它好像空气一样,是我们作为人类这种生命形态的一种框架。“时间小组”的各位在讨论时间问题时,是按照严格的哲学史对它进行概念的梳理。我无意说这样的做法有问题或者持批评态度,也不是把这个简单的和前面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论述联系起来。
进入关于时间的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本书:索恩–雷特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Macmillan, 1978)。这本书的主旨是有别于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观念史的思辨性精神问题的讨论提出一种不同的路径。在序言中他引用阿多诺(Theodore Adorno)的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存在或本体起源的回忆。”存在和本体是第一哲学经常讨论的问题,但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起源的回忆。这里已经涉及到时间性问题,时间不是当时当地的时间和空间的分析,而是意味着跨越时空,进行一种人类生产方式的根源性说明。

康德的先验的认识主体,是作为自明的命题展开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这样的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要做的是发现那些自明的命题的起源性的背景和关系。这类似于现象学排斥引经据典的研究、希望回到实事本身(den Sachen selbst),也就不是去讨论关于时间的理论,而是直接面对时间现象进行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在胡塞尔那里就是对于前谓词命题判断的精神意象的直观描述。这是我联系到刚才所说的这本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我们不可能像康德那样做一种自明公理似的陈述,我们只能将其视作一种发现。
2 生命与劳动的人类学
尤西林:今天我的讨论题目叫“生命与时间”。关于生命,可以把它延续或扩展到非人类的生命——自然的生命。最宽的视野指向热力学第二定理所说的熵。当温差被抹平,宇宙就会陷入一种冷寂的状态;而生命则是对于熵的矢量的抗争,即负熵运动。这种负熵运动,在不同的自然生命中,有不同的形态,而从人类学角度说,指的就是劳动,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负熵活动。它和自然的新陈代谢一起,维持着人的自然生命的更新。这样一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劳动的诞生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当劳动工具作为中介出现的时候。这也是黑格尔的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著名判断:当劳动工具作为中介出现的时候,人的欲望受到了遏制,因为这种欲望的享受需要延缓。这实际上就是人类学时间的起点。延缓意味着:人为了把握自己特有的劳动中介工具,必须后退一步,因而展开了一种时间。
如果只把使用中介工具的劳动看作是使用符号(最主要是语言)的活动,那么它既包含着使人和物“后退”的延缓,也意味着人必须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劳动。因此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后来被升格为伦理学。在人与人之间,也必须有一种由伦理的中介所导致的时间维度,它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了一种人类学的形态。马克思有一个命题:“时间是生命的积极尺度。”这个“尺度”不仅是规定和规范,而且也是意义的定位。时间绝不仅仅是操作性的度量;它眼下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性的时间。它的起源受正义这样的观念策动:时间一开始是作为正义,尔后获得了现代性的特征。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定位,与时间的规定结合,因而“尺度”对于生命而言不仅是一种静态的衡量,而且是动态的塑造。时间对身心的结构有质料意义上的作用。
时间的概念不是静态的认识论范畴,但是时间也不仅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生命的积极尺度。它也可以是消极的、负面的。这样的说法表明,马克思确实是现代性、甚至是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不仅生命是由时间作为尺度来塑造的;反过来,时间也是由生命来进行塑造的。时间和生命是相互塑造。
时间为什么是人类的必需的尺度呢?生命是一种自明的存在。但是时间的“出现”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呢?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行为,意味着中介的延伸和延迟。它产生了最初的时间尺度。
对于时间的理解,要与生命特有的人类学的劳动行为结合起来。我们不可想象一个孤身的、立在天地之间的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寻找到一种生命尺度的时间。从根源或本体起源的意义上说,时间一定来自群体的劳作。通过交流和传递,群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第一哲学的意义上,就构成了时间的尺度。
3 现代性的时间
尤西林:在古代的时间里,农业、牧业和渔业依赖自然生产的条件,因而它们的时间是不确定的、粗糙的,最重要的是循环的。这等于是依据着一种时间的框架来定位自己的活动的意义。
在以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活动特征:同质性。机器生产的“标准的”制造品,成为现代时间的原型。脱离手工的机械运动,保证了空前严格精确的标准件,标准件保证了时间的匀质性或同质性。这样的一种匀质性,表现在工序上,就是严格精准的、标准化的周期,这是时间计量单位的原型。资本主义的现代机械制造业,不仅是在工艺的技术条件上,而且是在观念形态的生产上,生产出了现代时间的计量。这一过程的象征就是机械钟表。机械钟表是观念依托着生产方式而完成的一种改变。生命劳动的尺度,与同质化的、标准化的“时间本身”开始分离。
这里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劳动目的的设定。劳动目的的设定,导致了技术程序的定位,由此才产生了面向未来的时间的分化。所有的时间,对于生产方式的终极存在或本体起源来说都是上位的。这种上位的时间,是在劳动的目的设定中才出现的。但是,如果这样的目的的实现是单一的、一次性的,它就并不会使时间的未来确定下来。只有周期性的、连续的劳动,才能使未来实现为现在的过程变成一种流动的程序。而在这种确定未来的周期性的实践中,通过“推移”,就会产生过去的维度。因而,时间的“三维”分化在劳动的生产方式中有它的终极本体和存在意义上的起源。
4 现代时间观的犹太起源
尤西林:这是不是说,人类的活动就只是劳动,人就只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我认为,在劳动中恰恰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经验,而这种精神经验首先就是时间的精神经验。这种时间的精神经验,首先是古代循环的圆形的时间观念,此后在人类历史的关键阶段又发生了逆转。这并不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某一思想家所定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文化与时间》(Louis Gardet et al., Cultures and Time, UNESCO Press, 1976)中很明确地确定了,人类的现代性的时间的起源在犹太人那里。

犹太教对现代时间观的独特贡献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经历巴比伦之囚亡国苦难的犹太人,数百年间挣扎于亡种亡教的边缘。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 מרד החשמונאים)胜利以后,复遭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 των Σελευκιδών)屠杀的事实,使犹太人最终放弃了对现实的希望。数百年的先知运动,都预言了弥赛亚(Messiah; מָשִׁיחַ)的来临,每次预言都包含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知道,时间地点越确定,越容易被证伪。而这次,在马加比兄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夜晚,犹太人在约旦河谷举起火把,向着天空高呼弥赛亚。
不要认为这只是犹太人的活动。我们知道,屈原在最后的绝望时刻的《天问》,问的也是这些终极问题。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所作的《理想国》里所说的最后的审判,亦是如此。在公元前夕,犹太民族形成了一种惨烈的弥赛亚期盼的心理结构,不再指望现世(现在)的公正与幸福,而认定一个善良正义而被害的弥赛亚必将死而复活,他将以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取代罪恶的旧世界。他们指望在一个未来的世界获得正义的审判。这个未来的世界是什么,当时还不明确;但是人类的时间观念就此展开为“两个世界”的观念。这样,必定到来的审判意味着未来被高度地“正义化”。它变成了正义审判的目标的象征,因而原本是圆形的时间被激进地“拉直”了。从此,人类的时间成了线性的、直线的、面向未来的时间运动。在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将基督教国教化的一百年之后,开始广为流行一个词:modernus,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但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时候是指时间的概念。Modernus的概念后来流行开来,规定了人们面向未来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使之进入现代性的时间,并且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史神学的根基。
公元410年,罗马城遭洗劫。面对着这一事件激起的世俗价值观的愤懑,奥古斯丁拉开了尘世之城(terrena civitas)和天上之城(civitas dei)这两个世界的距离,写下了《上帝之城》中的历史神学回答。奥氏回答的基点,是从道德–价值论而非知识角度反驳古代的循环时间观,并确立未来–目的论的时间观。幸福与公义的绝对实现在永恒循环的时间中无可期望,只有在期盼中,在未来时间的终点之外,才存在着至善。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神学之后直到今天,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哲学家,其中包括马克思。我们的未来就是共产主义,它实际上取代了未来的末日审判,是一种正义,意味着人的最终自由和全面发展。

5 历史的终结与对现代性的不满
尤西林: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冷战后两大意识形态的解体,此后出现了福山非常著名的一部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992)。很多人认为这个“历史终结”指的是共产主义苏联的终结,其实不然。这本书讲的是历史神学,谈到了奥古斯丁,也谈到了modernus这个词的演变史,它在基督徒的盼望中,就是末日审判。虽然绝大多数非基督徒没有这种观念,但是我们接受了文化和生产工艺结合的现代性的时间模式,而这个模式是由历史观念出发来论证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论证。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历史先行于时间。我们总是先接受了某种历史的观念,然后才获得了某种被视为天然、正常的时间观念。大多数人甚至可以不知道历史,但他们可以通过更切实的劳动的工艺方式被结合在一起。

这个劳动的工艺方式在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中的核心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讲的是在同一时间内、同样的平均的工艺和技术水准的衡量下,生产一单位的产品所需要花费的生命。生命的时间,成了劳动的计量单位。高速度是现代时间最为突出的特征,我们各项活动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的更新、加速所控制。
这引起了对现代性时间的非常明确的反抗。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索邦大学学生罢课,首先就是砸碎钟表、包括公共领域的钟表。这表明,现代性乃至现代化的时间,对人的生命成了一种压迫。因此,时间并非只是积极的尺度,也可以是负面的。
这种负面的尺度,今天比比皆是。现代时间激化了现代性的矛盾,引发了种种现代性批判,由此形成了时间的三维之间的种种关系模式,对时间的三个维度侧重不同:有的是要回到过去(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要回到传统的过去),有的是谈现在。把现代性等同于现在是一个大误解:现代性的时间,重点从来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它对于过程是不在乎的。
今天有人说我是后现代主义者。但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时间上的承继关系,而是逻辑上相互依存的关系。后现代实际上是要面对现代、超越现代。但是,这种超越恰恰属于现代性本身的机制。现代性意味着不断地超越现在、把它扬弃为过去,然后面向尚不在的未来,向前作直线的加速前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种种后现代批判,都如同希腊神话传说中那样,不断地为怪物输入魔力和营养。因而,后现代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它是现代的一个更加加速的版本,尽管后现代会最后分化为向空间的侧重,产生出时间观的革命性变化。
我更多地谈到现代性时间的一些负面效应,这绝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时间如同后现代主义者或贵族精神文化者说的那样,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对象。
6 自由时间要求制度性转变
尤西林:现代性的时间是生命的一种外在尺度。同时,时间也受生命的塑造。在自由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张力中,时间达到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形态。自由时间不再是为了复原下一轮劳动的休息,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开端。由此,一种自由的意识就会产生。但是,这样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节省下来的自由时间,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这里框架性前提是,没有哪一个个人可以独立地获得自由的时间,或者自由。自由的获得,或者说自由时间的真正转化(而非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后备军”的休息),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转变,需要通过社会和历史的方式完成。只有当一个社会使得每个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他人都当作目的本身和有自我的人格的时候,这个社会中人际交往、以及相应的人与物的关系,才会发生人性化的、真正有深度的奠基。而这样的制度建构需要现代性的时间作为我们生命劳动的尺度;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进程中继续前行。
7 母亲时间和父亲时间
尤西林:接下来探讨一下有关“母亲时间”和“父亲时间”的问题。我现在的关注点是母亲时间。女性的月经周期性地出现,它提供了来自自然生命的一种最初的时间节律。我们晚上睡觉、白天醒来,和地球的自转有关;而人的自然生命的诞生,和太阳照射的角度有特定的关系。由于这种先天的、自然生命的因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物钟。而生物钟和现代性时间的对抗,也是60年代之后很多文化哲学家转向与自然时间结盟的原因。
说到母亲时间,母体中的受精卵是人类共同体与伦理关系的原型。生命的孕育和期待,首先指向物性的“它”:还没有获得人类性的生命,这是动物意义的“它”。然后会有一个女性的“她”或者是男性的“他”。新生命的发育以对“它”、“她”、“他”的期待为中心,好像滚雪球一样吸引了全家人的期待。之后是分娩、哺乳,然后最早的人类学的介入就是语言和动作的发生。这样的一种人类学的发生导向的是我们所说的劳动。所以我同意李泽厚的如下判断: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作为20世纪的一个微观研究,印证了19世纪马克思的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好。
从十月怀胎、哺乳到怀抱成长,从家务劳作到教授语言这一人类学第一工具的传递,母亲的生命意义框架乃是环绕家庭终其一生的圆形时间。母亲的家务劳作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活动,它在古希腊由奴隶承担。家务活动的目标切近上手、基本无须中介。从煮食到洗涮,每一项琐屑的家务目标旋即消失于周而复始的消费之流中。母亲的家务活动毋需以强力克服阻力,因而母亲的行为没有暴力倾向。母亲的家务不建立持存之物,其简单重复的劳作被现代思想家视为人性中低级的“劳动”(labor)。承担这一无意义苦役的,却是母亲从受精卵开端的本体性的爱及其时间历程,这种生命的活动模式是由爱支撑的。而且,在这种爱中,它超越了一切外在的制度。
这样的圆形时间,可以与线性的父亲时间做比较。在人工智能到来后,父亲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因此,父亲将会“回家”。此后,母亲的时间将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时间。在当代人类面对现代性的弊病和人工智能的挑战时,母亲时间将会提供一种可能的人类生命自我塑造的时间尺度。

问题1
劳动与时间性何者在先?
黄裕生:首先澄清一下“时间小组”的方法论原则。梳理时间这个问题或概念在不同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那儿有何差异,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是想要通过考察不同的物理学家、哲学家如何直接面对时间问题,来启发我们自己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通过讨论,我们最后发现在物理领域中描述世界似乎不需要“时间”概念。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自然本身可以是“没有时间”的?
关于尤老师说的“劳动”,我承认,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尤其是对时间的量化,与劳动密切相关、甚至受劳动的塑造。我的问题是,劳动只有设置了目的才叫劳动,但是设置目的这个活动本身又有一个前提。这个目的是不在场的,或者是未完成的,或者是需要去完善的。我们竟然可以“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打开非在场的东西。只有不在场,它才会成为我们设置的目的、目标。因而,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向未来开放的时间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劳动也得以时间性为前提才是可能的?毕竟,连劳动都必须以已经能够打开未来为前提。
尤老师说,劳动是群体性的。我更愿意说劳动是社会性的,因为“群体性”的概念很难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人的劳动所要求的群体性是社会性的;社会性和一般的群体性的区别,在于社会性涉及合作,其中的分工者、承担者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承担起分给他(她)的任务;而动物完全是基于本能进行自然“分工”。也就是说,社会性的关系本身以独立自主地承担任务份额的能力为前提。组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性的群体,我们才能够进行劳动。但是,能够承担起任务的个体,又必须能够相互理解。相互理解(能够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对方、承认对方)又有一个前提,就是彼此有所期待和承诺。这是否也是一种作为前提的时间性?
尤老师的讲演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引入弥赛亚主义来解释现代性时间的来源。我们今天的时间观来自于希伯来文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来自于弥赛亚主义时间观,即现代性时间观。我们接受它,不是因为它简单地强迫我们接受。那么,为什么我们竟然会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来自特定民族的线性时间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性观念?
概括一下我想提的问题:
- 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时间”?圆形时间的确是人类在古代共同的时间观,古代的时间都是循环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观是不是就是自然的时间?循环的时间,是否就是一种陷在自然里的时间?
- 劳动本身以时间、意识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可以用来彻底解释时间。劳动可以把时间展开为各种形态,但是劳动本身是否要以原初的时间性为前提?
- 我们为什么无法摆脱来自于弥赛亚主义的时间观,即现代性时间观?现代(die Neuzeit)不是简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是朝向未来的。是不是可以说,不进入现代性,就没有未来?
尤西林: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已经证实,在人身上有自然的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晚上睡觉,白天醒来,这和动物界、植物界一样,是由于地球自转、昼夜交替所导致的。至于人可以晚上干活,看似突破了这一点,但这恰恰是在现在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强制下、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如果从自然的角度看,人晚上要睡觉,白天要醒来,这就是自然的时间。
有没有“纯粹”的自然时间?我先前说的母亲的爱,在很多动物身上也能看到。我们当然不可以用拟人化的方式把动物和人等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和动物在自然的意义上有连续性、关联性。
有关第二个问题(劳动设定目的,而对目的的设定一定要引入未来时间),我的观点是:所有的未来时间的成型,是和最初的劳动的发生点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个发生点,黑格尔这样说:人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第一个要去抓取把握的不是别的,而是工具;这和狮子第一个要捕捉的是羚羊是不一样的。人必须抓着一个本身不能吃的棍子,延长四肢,来击打树上的水果。这样的行为使棍子成为他和他的消费对象之间的中介。所以黑格尔说,中介是有尊严的,它高于直接的享受,所以锄头高于谷物。这样的工具带来的时间延迟,就是时间的发生。而未来的时间,就是在这种对劳动工具(中介)的使用之中,日益得以扩展和深化,得以积累和分化;此后,才能产生明确的目的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于一切古典意义上的存在论和本体论起源的回忆。回忆在这里就是对根源性的活动的说明,而不是寻找康德意义上的自明的先验前提、把它作为一个命题确定下来。
与此相应地,人类已经获得了一些很成熟的、受到强化的、定型了的时间意识。成熟的人能够对时间的三维采取不同态度,能够设定目的,这种设定仿佛是下意识的。但这恰恰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它指向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目的在意识中的设定,还是对于时间的三维的分化,并非是一蹴而就,而只能经由一个历史过程形成。时间的三维、对目的的设定,对人而言并非向来如此,也未必永远如此。
这里的“永远如此”,面临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现在由于人对物的关系被人工智能大量取代,生产方式中的另一大部分就变得突出,这就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后一部分最后被转化成了“交往”,因此,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最主要就是要通过交往理论来实现。他这样做,依据的是当代的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反过来,我想说的是:所有可以变化的东西和要形成的东西,是要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再生产的劳动,生命就不能进入某个时间尺度的框架,不能获得一种意义定位。如果那样,人向未来的开放、对目标的设定,包括人性中其它高级的精神特性,都会日渐萎缩。

问题2
时间对每个人是否等同?
黄藤(西安外事学院):在同一“客观”时间内,每个人所经历的时间是否是对等的?比如,现在我和尤老师的时间是不是等同的?
尤西林:这涉及时间的个性化问题。在现代性时间带来的反思、以及时间的三维之间激烈的冲突中,使人们提出了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化的要求。每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工作方式中,希望有新的、适合自己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和塑造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个意义上与自己的时间尺度形成了一种非常友好的相互关系。今天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和塑造自己的生命的人,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好的生活背景的人,需要很高的精神觉悟,只有这样,他才能采取自己的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生活。
关于时间是否有可比性的问题:时间的可比性是在平均的劳动时间中得到奠基的,它最后就被转化为一种最简单的对应物:货币。货币实际上是对时间的封装:用货币购买就是用平均劳动时间去交换。在人类的交换活动中,这始终是奠基性的。由于有这样的可交换性,时间必然会获得可公度性。
问题3
“母亲时间”基于循环的宽恕能力是否有限度?
刘任翔:尤老师对时间的问题的讨论,脱出了哲学、科学的抽象的概念框架。讲演的标题是《生命与时间》,我觉得也可以叫做《劳动与时间》,前提是以尤老师这种非常宽泛的方式去定义劳动:创造性的,能够产生延迟的、能够展开过去和未来的、群体性的人类活动。
关于尤老师和黄老师的争论,我觉得双方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而双方都有把对方所倚重的东西给“现成化”的倾向。当黄老师说首先要有时间才能有劳动的时候,是对劳动作了现成化的理解,把它当成人类参与的诸活动之一。而当尤老师说只有有劳动才能有时间,也是把时间当成了现成化理解的“流俗”时间,而劳动反而成了原初的、发生性的层面。无论我们从哪里出发,我们的一项共识是:要回到胡塞尔所说的那个“原初经验”的层面,回到起源、本原。这不同于历史上某一点实际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此考察的历史已经预设了历史的时间性。相反,我们说的是一种直到今天还要不停地激活的经验,它潜藏于(比如说)对钟表时间不假思索的预设之下。哲学的追问,只是在挖掘这种经验。
我想集中讨论一下尤老师提到“母亲时间”。首先,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母亲时间”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母亲都只存在于这种时间性里,也不意味着这种时间性仅限于母亲这种角色。它只是说,我们在关于“母亲”的传统形象里,能够较为典型地体认到这种时间性。
根据尤老师的说法,“母亲时间”包含了一些我们平时都会觉得是循环、重复的东西,如“洗洗涮涮”。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粹的惰性、意味着缺乏创造性。但是,尤老师的工作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循环和惰性给区分开了。循坏不是完全不动,而是能够不断回归。
循环活动所赋予人的回归的能力,尤老师是以“爱”这个概念来表达的。如果把讨论放到阿伦特《人的境况》的语境中,我认为这种能力也可以用“宽恕”这个概念来捕捉。这是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的宽恕:不仅仅能够宽恕一个做错事情的人,也能够宽恕(比如说)我们通过现代技术、乃至通过人工智能这种不断地向外、向未来投射的技术所走入的迷途。在依循尤老师所说的“父亲时间”而走入这些迷途之后,我们可能恰恰需要“母亲时间”循环的更新能力,来给这种迷途以宽恕。宽恕的意思就是说,尽管我们可能会犯错误,但是由于我们拥有这种从生命而来的最基本的循环性,我们可以以生命那常新的“韧劲”来承受、乃至包容某些不好的后果,把它们纳入到历史叙事之中,纳入人性的深度之中。

不过,“母亲时间”的这种出于循环性的宽恕或爱的能力,是否有个限度?是否会存在一种线性的技术,使得我们彻底突破了循环时间所能够宽恕的范围,使我们万劫不复地走入某种没有办法再走“回头路”的境地?
尤西林:在父亲时间所统治的整体的人类学处境中,母亲时间也发生了双重化。母亲在家里是这样的,但是一旦走出家门,她也可以加入父亲(时间)。我指的不是任何特定的一种社会角色,而是人类学所说的自然性别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上的塑造。这种塑造尽管有可能双重化,它仍然保留着基本的圆形时间和以爱为中心的、基于自然之爱的人类学意义。在今后的生产方式的更新中,在人们的新的交往模式中,圆形时间会成为一种资源。在深度的哲学意义上,异化最少的恰恰是那些在家里恪守妇道的人;而在现代性的这种生产方式中,被伤害最深的是那些进入职场的女性。当然,这里指的是同一性别角色内的比较。如果把女性放在现实的社会处境中,我们会看到她有多重的发展可能。我只是就她的一种可能角色来讨论。
问题4
线性时间、线性史观、现代性能否等同?
成果:我对尤老师讲的线性时间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质疑。按照我的理解,线性时间和线性的历史观是两回事。线性时间的观念,是通过自然、通过对于生命有限性的体验,就可以获得的。
在此基础上,人们有了不同的历史意识:一种是循环的历史意识,一种是线性的、不可逆的历史意识。但如果我们就这种线性的历史意识来说的话,在宗教学层面不能说仅仅犹太人具有它。犹太人的线性历史观可以表述为:我们起初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或原初状态,后来我们自行堕落,在有限性中受苦。在受苦中,出现了所谓末世论(eschatology)的教导:终有一天受苦的状况会终结,我们可以从受苦的、有限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没有时间的或超时间的状态。在比如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佛教、印度教、甚至希腊的俄耳甫斯教(Orphism)当中,都有类似的表述。

虽然这些宗教都基于线性时间的观念,甚至任何普通人通过自然的认识也可以获得对线性时间的一些模糊观念,但是犹太教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通过这种线性的历史,把它的整个神话给构建起来。这可能是别的宗教所没有的。换言之,犹太人的线性历史观是在一个普遍的萌芽的基础上,个别地乃至偶然地成长出来的。
再者,尤老师似乎把线性的时间和现代性直接等同起来。但是我认为,线性时间和现代性之间还是有一个界限,它关乎对未来的态度。即便发现了线性时间观,最关键的区别还是在于对未来是采取一种消极的、等待的态度,还是主动去创造这个未来。这是现代和古代最根本的区别。黑格尔和谢林,像尤老师一样把犹太–基督教和异教对立了起来,认为前者是现代性的萌芽。但是他们认为,基督教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前现代的基督教对未来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态度。黑格尔和谢林认为,时间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而且是一种处世或生存态度,所以只有把未来的向度(或者说时间性)给扬弃之后,才能恢复勇敢,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有积极的作为。这一点在康德那里就明确地确立起来了。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不认同尤老师有关“共产主义是最后审判的简单替代”的观点。我认为中间还有康德、黑格尔等人引发的现代性转向的问题。
尤西林:成果提到在轴心时代的其它的一些宗教中也有与犹太教相仿的线性历史观的萌芽,这我完全赞同。我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弥赛亚主义的盼望,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死而复活。这个问题原来在犹太教中是没有的,是从波斯那儿传过来的。当时很多宗教的观念是互相借鉴、渗透的,因此他们共同的历史观念、包括对未来的信念,都是相通的。但是,在犹太的弥赛亚盼望中,这种信念得以更纯粹地普适化;经由泛希腊化,它最后变成跨欧亚两洲的文化和文明的交织。在这样的社会生产背景下,一种宗教和文化的信仰才变成了有力量的东西,而不是由于孤立来看的观念本身的合理性或感召性。
问题5
自由高于时间吗?
听众:尤老师之前提到,历史性先于时间性。那么历史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认为这和自由有关。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承认自由高于时间?
黄裕生: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时间问题最终引向自由问题。之所以会有时间这回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跳出自然、跳出必然性,而打开可能性。这样才会有时间问题。否则,就跟物理世界一样:物理世界有运动、有变化,但没有时间问题。
我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发生学,或归为某种物质的运动,或归于人的生物性的、自然性的活动。甚至我也不认为用劳动可以解释人类的一切。劳动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不一定在时间上先于劳动,但在逻辑上要先于劳动。
换一个维度说,即便我们承认进化论,承认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这个进化的过程中仍是有中断的。中断点就在于,我们彻底告别了自然的限定,跳出了必然性,跳出了自然现有的东西。我们能看到、理解到自然中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与自然中断的一个标志。而这恰恰就是自由;我现在更愿意把它归于自由的一个“开端”,或者说,我们真正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非自然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基于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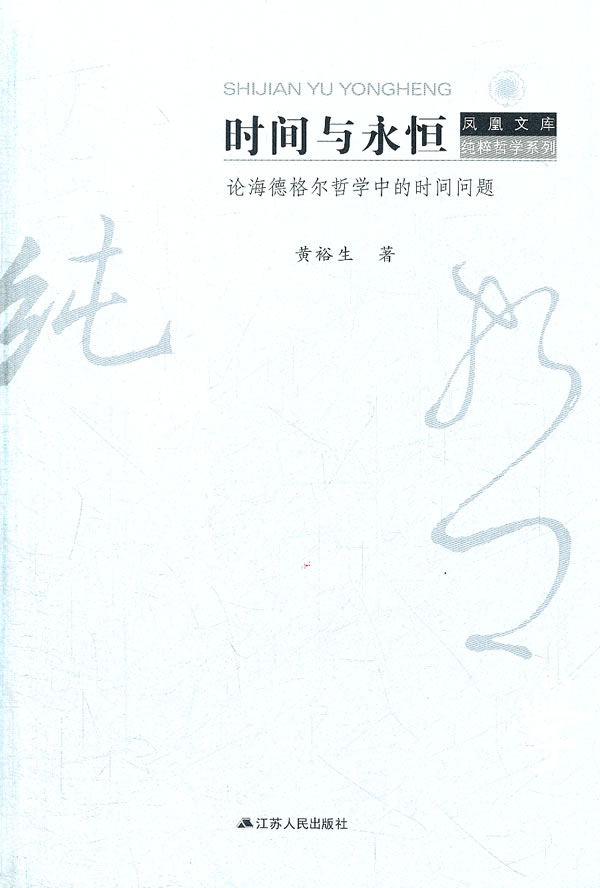
其他听众提问
- 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得一种“时间的质感”,就是人自身和自然、事物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人与时间也是完全融合的。会感受不到时间,不会去看几点了、掐表、数时间。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与时间分离的,对时间的感觉也很机械。怎么办?
- 如果时间和现代性的产生与既定的社会生产周期以及未来所具有的值得期待的超越性相关联,那么像疫情这种未来不可知的灾难的出现,会对人的现代性和对时间的认知有什么影响呢?
- 如何看待母亲的循环时间与现代性时间框架的冲突?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经称女性的时间为“在时间之外”,这种在线性时间之外的活动模式如何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新的可能?
- “母亲”的爱,是否也预设了一种自主性,从而不是简单的循环时间所能支撑?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就是圆形时间,每个人都有圆形时间,为何要把它限于“母亲”的角色?